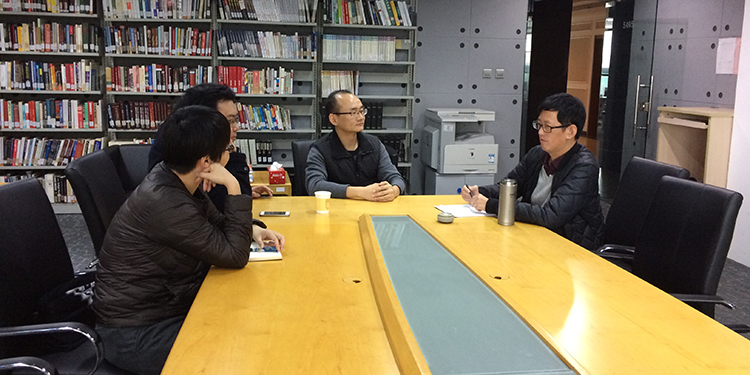
1月10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美國海外核部署研究”舉行項目沙龍。本次沙龍由項目負責人陳波副教授主持,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後遊覽🙂↕️、劉曉晨和博士生藺曉林參加了活動🫃🏻🌹。
項目負責人陳波老師介紹了最近的研究成果💇♂️:肯尼迪政府與南越1963年危機。應該說,這一課題在美國的越南戰爭史研究中屬於比較成熟的題目,但美國最近解密了肯尼迪總統的重要會議錄音文件,這為從史料上對以往成果進行批判性研究提供了可能。陳波首先介紹了美國越戰史學的狀況©️。美國的越戰史學(Vietnam War historiography)是一個宏大的、值得關註的課題。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史學界圍繞越南戰爭形成了兩個相對應的流派➛:傳統派(orthodoxy school)和修正派(revisionism school)🛅。傳統派是在越戰給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帶來沖擊的20世紀60🧘🏽♀️、70年代興起的,又與當時的社會👩🏻🔧、輿論和文化運動相聯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當時媒體報道、評論人觀點甚至現代傳媒技術的影響🧖🏽♀️。比如🦇,最早批評肯尼迪的越南政策的🫴🏻,是與越戰糾葛頗深的紐約時報著名記者大衛·哈伯斯坦,他的《陷入泥潭:肯尼迪時期的美國與越南》除了批評美國的越南政策之外👩🏿🦱🍹,尤其對吳庭艷政權不滿。此後✧,切斯特·庫珀的《失敗的征討☛:越戰中的美國》和斯坦利·卡諾的《越南戰爭:一部歷史》,用更多的細節講述美國對越南政策的失敗🤵🏽,加布裏爾·科爾克的《透視戰爭🧑🏼💼:越南、美國與現代歷史》則進一步指出越戰是試圖向世界強加“美國秩序”的結果。傳統學派認為美國註定在越南失敗🪠,是個“錯誤”和“悲劇”。越戰錯誤的形成有兩個原因:一是以冷戰對抗的邏輯選擇了南越作為扶植的對象;二是逐步以軍事手段取代了政治手段。修正派的出現與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變化相契合,是社會保守力量對60年代自由主義歷史書寫的一種回應👌👩🌾。到了80年代末,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美國國內的保守主義再度高漲,從而在史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一些對以往重大歷史事件再研究的“修正”觀點,特別是美國在二戰後的地位以及“帝國主義”形象得到了修復。以越戰為例🏊🏿♀️,修正派學者認為傳統派觀點長期浸染和影響美國史學,美國在越南的行為形成了一張“道德可疑的臉譜”🤘🏻,一種“必然失敗的成見”🏂🏼。在他們看來🧖♀️,如果美國的道德和物質優越性“毋庸置疑”的話,那麽越戰的失敗就是內部問題了:政府內部的自由派分子🦸🏻♂️、媒體以及反戰運動等等🛤。例如🧗🏼♂️🪔,修正學派代表人物京特·萊維的《美國與越南》對傳統派的“意識形態狂熱”並不認同🙌🏿,認為美國遏製共產主義的政策無可厚非🎈。修正派另一代表人物哈利·薩默的《論戰略:對越戰的批判分析》從軍事的角度觀察越戰,認為美國在越戰中的問題在於背離了美國傳統,過於被當時的國際政治所左右。邁克爾·林德的《越戰🚶♂️➡️:一場必要的戰爭》也是修正派的代表作品🤱,認為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其動機和邏輯是合理的,但具體手段值得商榷。修正派人數不多且處於守勢,總體上把越戰看作是必要的👨🏽🦱,也是有成功的可能的🙇。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的越戰研究以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為參照🕵️,有了新的認識👨🏼⚖️。加上新史料出現和新史學方法的運用,傳統學派的觀點又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弗萊德裏克·羅格威爾的《選擇戰爭:喪失和平之機與越戰升級》,認為越戰不可避免並非是冷戰觀念導致的必然結果,而是因為約翰遜和他的顧問們因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將美國領入絕境🤿。馬克·布雷德利的《越南和美國的相互想象:獨立越南之形成,1919-1950》,試圖擺脫美國為中心的視角,將越南本身納入考察的範圍🫷🏼,認為美國和越南的行為更多地是受到了對對方“想象”的影響👮🏽,而不是對方實際本身。賽斯·雅各布的《美國在越南的奇跡人物:吳庭艷、宗教🫰🏼、種族和美國對東南亞的幹預》將美國支持吳庭艷的原因歸結於文化和宗教原因🐯。無論是政客們的權力欲𓀃👩🦳、美國對越南的想象與誤讀,還是與南越的宗教聯系,以上三位研究者雖然努力從“冷戰邏輯”之外來解讀👱🏿♂️,但在本質上仍然屬於傳統派。馬克·莫亞的《被遺棄的勝利👳🏽♀️:越南戰爭史,1954-1965》是新世紀修正學派的又一代表作👉,認為越南革命應該被遏製😧😩,吳庭艷是一個有能力的統治者🏢,美國卷入越南也是“正確的”。美國和南越的軍事行動在阻止越共方面也是有成效的,反而是美國媒體對一些事件的報道,誤導公眾和一些政府人員認為這個政權瀕臨崩潰。莫亞認為恰恰是支持政變推翻吳庭艷政權的“錯誤決定”斷送了即將取得勝利的反遊擊戰🤳🏼,從此南越局勢陷入混亂,美國不得不派軍隊進入越南🧑🏻🚀。
就史料而言🐵,1963年南越危機也體現了學者們對越南戰爭具體問題的持續關註。1971年被媒體披露的《五角大樓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專門有一部分涉及南越危機中美國政府的反應與政策😶🌫️。2011年,該文件完全解密,為全面解讀這些史料提供了可能性。除此之外✨,《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FRUS)、電子數據庫“美國政府解密檔案參考系統”(DDRS)和“國家安全數字化檔案”(DNSA)等傳統美國外交史料也是重要的資料來源。值得關註的是⬅️,美國國家安全檔案數據庫(NSA)曾在2003年、2009年和2013年分三次解密危機期間美國政府關鍵性文件,甚至包含了史料的比較分析。尤其是2013年解密的1963年8月底幾次重要內閣及白宮會議的錄音和會議記錄文件🤚,為學者更為確切地了解美國高層👒🏊🏼♂️,特別是肯尼迪總統本人對軍事政變的態度變化、在政變過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更多、更直接🧍🏻♂️🙆🏻、更富批判性的史料依據。
目前從事的這一課題對美國外交史研究,有三個層次的意義:1)對美國外交決策機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包括政府高層官員的內部分歧及成因🥌;2)美國外交政策存在的價值困境,即時常會陷入一種自身的現實考量與價值訴求帶來的尷尬境地🧘🏼♂️,無法擺脫國家安全利益與意識形態目標的選擇困境👩👧🤷🏿♀️;3)檔案材料的多元化與文本史料的批判使用💮,特別是錄音材料的比對與互證要求研究者對文本史料存在的“陷阱”有甄別和批判能力。

